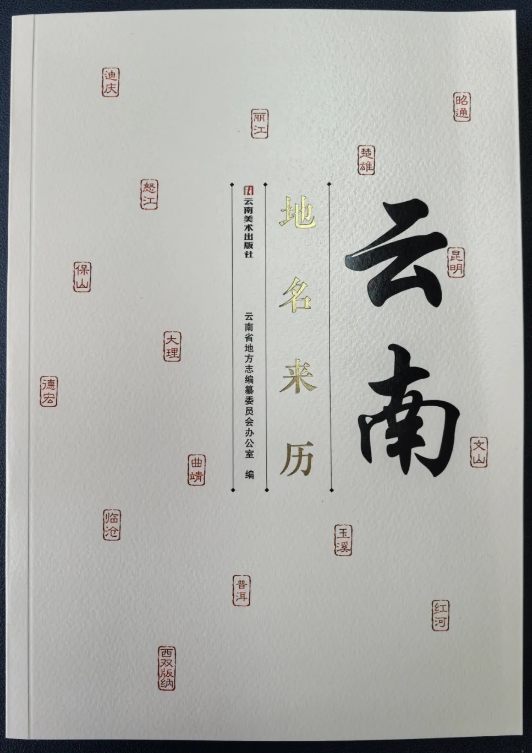
云南地名来历
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
编者按
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把解锁山河的密钥,是时光刻在大地上的密语。云南,这片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交错的土地,因26个世居民族的共生共融、千年茶马古道的驼铃回响,孕育出中国最斑斓多元的地名文化图谱。
自“昆明”的山河变迁到“西双版纳”的傣家月光,从“香格里拉”的雪山圣境到“普洱”的茶汤记忆,云南省—16州市—129县(市区)共146个三级行政区地名如同146粒文化琥珀,封存着古滇国的青铜回响、南诏大理的梵音往事、戍边移民的乡愁密码。我们以地方志为舟楫,溯流历史长河——考据典籍钩沉,踏访古道遗迹,聆听乡老口传,在民族语言的音韵褶皱里,在戍边屯垦的碑刻纹路中,在山河形胜的地理肌理间,解码每个地名背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。
即日起,让我们循着地名的星图,以146个地名的来历为线索,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云南文化巡礼。从今天起,“云南地方志”微信公众号每周一为您更新一篇《云南地名来历》,当您轻触屏幕翻阅这些故事时,指尖流淌的不仅是汉字的形意之美,更是云岭大地上永不褪色的山河记忆与人文精魄。欢迎在字里行间,遇见您魂牵梦萦的故乡。
前言
地名,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,或指明其空间方位,或归纳其地理类型,或反映其地理特征。地名既是对一个地方自然环境的描述,也体现出对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与时空想象或精神寄托与美好向往。
2023年6月2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,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。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,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,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,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而地名,既是文化符号,也是文化载体。
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,山川秀丽,民族众多,文化灿烂,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悠久的历史文化,辉煌的近现代史,在云南一脉相承、历久弥新,为云南各族人民奋勇前行提供着不竭动力。
地名是山水的映像,描绘着人与自然的交融历程。“去城之东百举,有江横绝曰盘龙”,便称此地为盘龙;澜沧江上“夜覆云雾,晨则渐以升起,如龙”,云龙一名由此诞生;三山环绕,山脚平整,有田有水,似蓄墨砚池,故名砚山。茫茫山河润泽土地,养育人民;人民又以文字和口述史记土地、 忆家乡,把炙热的情感融在名字里,把生活过的土地放在魂魄里。
地名是历史的印迹,保存着人与土地的记忆。比如晋宁,其地名可追溯到西晋,原为祈望晋朝统治长治久安之义,却一直沿用了1700多年之久;又如会泽,1725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云贵川施行改土归流政策时,此地由雍正帝亲自取 名;再比如水富,直到1974年才得名,2019年才设立县级市,地名中蕴含着一段互帮互助调整行政区划的佳话。
地名也是文明的映射,构造着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。一些地名也许用词简单,但背后凝结着人与地、地与物、物与事的关系。一些地名记录了战乱与迁徙,经过数代人的口耳相传, 仍能引人冥想。“平”“安”“富”“宁”“康”“昌”等祈福之词在地名中被广泛使用,反映着人们朴素的愿望,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。此外,云南还有不少彝语、傣语、白语等民族语音译地名,多民族文化在云南的土地上和谐共生,走向世界。
除史籍资料外,本书在编写中还加入了民族口述史、民族语言学、现代地理水文考察等领域的最新资料,力求展示每个地方在历史、人文、社会、自然等方面的特殊唯一性,做到集权威性、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,使云岭之风土人情、地名文化跃然纸上。
本书对于不同的地名来源,采取“异说并举”的方法。以昆明为例,其名来源有彝语“地名说”、白语“地名 说”“因池得名说”“描绘气象说”;又如双柏,有“西汉 县衙古柏树说”、有彝语“龙潭城镇说”、彝语“金山财水说”;再如马龙,有“地缘说”“文学说”,以及彝语“地名说”。总之,《云南地名来历》集诸家之说,汇多源之考,力求完整客观记录传承云南的地名文化。
最后,回到“云南”这一名称的来源。书中梳理了“云南”这一名称从西汉以来作为行政区名一直沿用至今的历史,但是“彩云南现说”“云岭说”“民族语改易地名说” 等在诸多文献中大体沿袭旧说,无从考证。所以,对于“云南”的来历、含义,本书只梳理记载,不做定论。
云南省——中国地名百花园
云南,是一个地貌独特、物产丰富、气候宜人的省份;地处边疆, 历史发展自成脉络又与中原文化保持紧密互动;多民族文化共存,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,独具生机活力,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。
云南位于中国西南方,全省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,地形类型极为多 样化。红河及云岭以东为滇中高原,以西可分为滇西北高山峡谷、滇西中山宽谷、滇西南山原、哀牢山地。区域内深大断裂带十分发达,它们控制着地貌的格局和山河分布大势,形成主要由丘陵状高原面和分割高原面交错构成的多山的高原地貌。北部与中部有许多磅礴的山脉蜿蜒绵亘,主要有云岭、怒山、高黎贡山、无量山、点苍山、哀牢山、乌蒙山、拱王山、大白草岭、小白草岭、药山等。这些山脉大体呈现为西北向东南扩展,导引境内江河自西北往东面、东南、南面展开,成帚状水系。海拔四五千米甚至更高的山岭,一年中有很长时段都可看到茫茫无垠的冰雪景象,比如滇藏界上的梅里雪山、耸峙金沙江两岸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、雄踞滇东北的轿子山等。山与山之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盆地(坝 子),比如滇池坝子、陆良坝子、祥云坝子、大理坝子、曲靖坝子等等。境内的崇山峻岭间,奔流着众多的河流,它们分属金沙江、珠江、元江、澜沧江、怒江和伊洛瓦底江六大水系。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,进入省境西北部后,呈“川”字形自北而南纵流。金沙江在石鼓掉头东转,迂回穿行于川滇之间。澜沧江、怒江一路奔腾向南,流到境外。珠江上游南北两盘江在滇东北、滇东、滇南迂回盘曲,斜贯省境中部的元江流入越南,滇西和滇西北的一些河流汇入缅甸的伊洛瓦底江。在这片高原的一处处低洼地带,还镶嵌着众多明珠般旖旎的高原断层湖泊。它们有的叫湖,有的称“池”,还有的名“海”,其中水域面积最大的为昆明的滇池,大理苍山之麓有全省第二大湖泊洱海,其他称“海”的还有滇中的阳宗海、滇西北的程海等,称“湖”的则有抚仙湖、星云湖、杞麓湖、异龙湖、泸沽湖等。
“云南”这一名称是怎么来的呢?它的源头是一个县名。
西汉元封二年(前109)在今云南置益州郡,辖有云南县(今祥云县),“云南”二字作为地名始现史籍。东汉永平十二年(69)后,云南县隶属新设的永昌郡。蜀汉建兴三年(225)云南县改属云南郡。唐武德四年(621),于今云南境内设置姚州。唐开元二十六年(738),蒙舍诏部落酋长皮罗阁建立南诏国,被封为云南王,设云南安抚司。宋代封授大理政权的统治者为云南节度使。南诏、大理兴盛时期,其疆域包括今云南全省及贵州西部、四川南部,还有今缅甸、泰国、老挝、越南的部分地方。因此,唐宋时期的“云南”,地域比今广阔。当时的一些著述中,将这些区域也冠以“云南”的名号,例如唐代韦琯的《云南事状》、窦滂的《云南别录》、樊绰的《云南志》(也称《蛮书》),宋人辛怡显的《云南 录》、杨佐的《云南买马记》。元至元十三年(1276),将今天云南为主体并包括四川、贵州一部分和境外大片地方的一个广大区域设置为一个行省,因袭唐宋以来已经习惯而流行的叫法,定名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,简称云南行省。此后,“云南”作为省区之名一直沿而未变。
为什么叫“云南”?它的含义又是什么?
“云南”作为行政区名,虽然在西汉便已出现,但是今天能读到的汉代文献,对此命名未作解释。此后直至南诏、大理国,官修或私人撰述的文献中,依旧没有解释。元代文献中,出现了彩云南现说。按《元史·地理志》等书的记载,南诏、大理国时期改原云南县为云南州,又曾称过镜州。元《混一方舆胜览》说:“云南县,古镜州也……张乐进求时,五色云现,州在云南,故名。”这是关于“云南”含义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说法,这种说法中提到的“张乐进求”,与蒙舍诏诏主细奴逻为同时代 人,大约生活在6世纪末至7世纪中期。明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》记载云南州时有类似的说法,且更进一步,天现瑞云被说成经常出现的现象:“谓常有庆云现于州之南,故名云南。”《万历云南通志·地理志》把“彩 云”时间再往前推到了西汉中期,说道:“汉武元狩间,彩云见于南中, 遣使迹之,云南之名始此”。此后,谢肇淛《滇略》等诸多文献大体沿 袭此说。彩云南现的传说,被很多人认为是“云南”得名的缘由,但这种说法出现在“云南”之名问世的千年之后,所说西汉彩云南现或张乐进求时五色云现之事,据传世的汉唐文献更是无从考证。从情感认同的角度, 人们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,但严格讲它当然不能成为定论,相反颇有臆度附会之嫌。“云南”来历、含义的另一种说法,源于南朝梁刘昭,他注释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云南县说:“《南中志》曰:县西北数百十里有山, 众山之中特高大,状如扶风太一,郁然高峻,与云气相连接,因视之不 见。”近代以来,一些知名学者据此认为,“云南”正是因此而得名,意即云岭(云气缭绕的高山)之南或云山(鸡足山)之南。然而,由刘昭注而转圜出来的这种解释,不免牵强。综合各种因素看,“云南”为当时今洱海以东一带土著民族语音译的可能性更大,只是具体含义已无从考证。云南又简称滇,这是因为先秦至秦汉时期今滇中一带活动着滇部族,并建立滇国。“滇”的来历含义,迄今众说纷纭。一是将“滇”与滇池 联系起来解释,最早的是刘逵注释《文选·蜀都赋》引谯周《异物志》 所说:“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,似如倒流,故俗云滇池”;又如清王先 谦《汉书补注》说:“颠与滇同,以颠主义,顶也,皆因滇池居地高巅 之故”;刘琳《华阳国志校注》说:“盖滇本当地少数民族对此湖(指滇池——引者)的称呼,汉人译其音加水旁作滇耳。”近几十年来,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:李乔《从滇谈起》提出“滇是古代一个土著民族的名 称”;林超民《漫谈滇的来源》认为滇来源于羌人中一个部落首领的姓 氏,后用作部落名;孟平《滇来源的质疑》主张“滇”是今彝族先民的语言,近似于今彝语“甸”,意即大坝子;张庆培《滇的由来与彝文文献〈勒俄特依〉中的“滇濮殊罗”考》认为滇即古彝语滇濮殊罗,“滇”为“鹰”,“濮”为祖人或族,“殊罗”为深大的湖泊,全意为鹰族的大湖或滇濮族的大湖;张竹邦《滇的语种与含义初析》提出滇为傣族先民,源于梵语“禅”。“滇”的来历、含义虽然还难作定论,但它很大可能是当时今滇中一带民族语的音译,不应从汉语角度去解说。
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中,云南一直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,每个时代都有许多民族活动在这片舞台,并诞生了用他们的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。最早记录云南古代非汉语地名的典籍为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以后直至明清, 历代文献中都记载了不同数量的非汉语地名。总体上说,越往后文献记载的越多,它们包括政区地名、居民点地名、交通地名、山川地名等等。当然,由于各种因素,古代更多的非汉语地名没有被文献记载下来。
当今,全省境内除汉族以外世居着25个少数民族,有较多地区都保 留以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,云南因此而成为全国民族语地名语种最多的省。按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结果的统计,全省地名共计49万余条,其中彝语地名21793条,占所有少数民族语地名的32.03%;傣语地名19949条,占29.32%;藏语地名4810条,占7.07%;壮语地名4354条,占6.40%;傈僳语地名4317条,占6.35%;哈尼语地名3872条,占5.69%;纳西语地 名2544条,占3.74%;佤语地名1468条,占2.16%;白语地名1175条,占1.73%;景颇语地名1025条,占1.51%;拉祜语地名851条,占1.25%;怒语地名650条,占0.96%;独龙语地名530条,占0.78%;藏汉复合语地名484条,占0.71%;傈僳汉复合语地名213条,占0.31%。此外,还有基诺 语、普米语、布朗语、德昂语、阿昌语、苗语、布依语、水语、蒙古语、满语等语种的地名。这些民族语地名在广袤的大地上交错分布在全省各区域,且分布密度悬殊很大。很多语种的地名呈现为大分散、小集中的分布状态。全省12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,绝大多数都有民族语地名,全为汉语地名的地区,仅东北边缘的昭通市水富市与绥江县两地。西北部的民族语地名比例最高,西部、南部边缘多数县市的比例也较高,滇中、滇东、滇东北总体比例低一些。

云南少数民族语地名是自然与历史人文的结晶,是民族文化的珍贵 宝藏。这些地名是各民族语言的活化石,它们储存地方历史,反映地理环境,记载民族分布或迁徙的信息,也承载着民族群众的观念与思想,还往往是民族生活情态的写照。云南省内来源于上述历史、地理等各种情形的地名,都有一定的数量。有些地名甚至具有综合多方面的文化内涵。
这些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:第一类是地理环境,以小范围内特殊的地形地貌命名;第二类是特产风物,以野生动植物,包括野果、野菜、怪树、野兽等命名;第三类是历史遗存,以民族的生存、迁徙、发展等命名;第四类是反映生活,如歇息、玩耍、被骗、进行交易、奋起反抗坏人坏事等场景命名;第五类是宗教信仰或神话故事,以傣族语和藏族语地名最多,并且随故事路线形成系列;第六类为名号或姓氏,此类地名占有相当的数量,他们以某部族或民族的首领、英雄或长者、家支等的名号命名,或以某某姓氏命名。
(来源:云南地方志)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271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271号